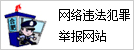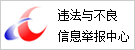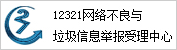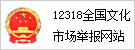中國當(dāng)前大多新建劇場(chǎng)的舞臺(tái)基礎(chǔ)設(shè)備相比于國際水平都不算差,但為什么我們總會(huì)感覺呈現(xiàn)的舞臺(tái)效果差強(qiáng)人意?差的是從手工業(yè)到工業(yè)發(fā)展的那非常關(guān)鍵的一道門檻。這道門檻,往往不是設(shè)備,而是如何運(yùn)用這些設(shè)備,如何理解這些技術(shù),如何將舞臺(tái)制作看作一個(gè)齒輪式彼此銜接的過程,完成工業(yè)的運(yùn)作。從這個(gè)角度去看,以“奢侈”的方式引進(jìn)《戰(zhàn)馬》,對(duì)于我們理解什么叫舞臺(tái)工業(yè),應(yīng)當(dāng)說是在關(guān)鍵時(shí)刻起到關(guān)鍵作用的。
馴服舞臺(tái)上的鋼鐵
《戰(zhàn)馬》在今天的意義,是要將其置于中國文化/戲劇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過程中去觀察的。
文化產(chǎn)業(yè),嚷嚷了很多年。可大家熱衷討論的“產(chǎn)業(yè)”,要不聚焦于作品/產(chǎn)品能不能“大賣”,要不就是聚焦于投融資。投融資是產(chǎn)業(yè)的前端,消費(fèi)是產(chǎn)業(yè)的末端,而文化產(chǎn)業(yè),是要以文化生產(chǎn)的工業(yè)化為基礎(chǔ)的。沒有強(qiáng)大、完整的工業(yè)體系,產(chǎn)業(yè)是很難壯大的。這一問題,在其他經(jīng)濟(jì)領(lǐng)域中應(yīng)當(dāng)是最容易理解的,但到文化領(lǐng)域,就變得很模糊很曖昧――是不是文化搭上產(chǎn)業(yè)已經(jīng)顯得很掉價(jià),還要談工業(yè),就更有點(diǎn)難以啟齒呢?
幾年前我在哥倫比亞大學(xué)訪學(xué),有機(jī)會(huì)跟著哥大戲劇系的本科生到處去看戲。很多戲在講什么,我大多都忘了,但關(guān)于百老匯乃至外百老匯的有一點(diǎn)印象極其深刻――那就是舞臺(tái)制作的強(qiáng)大能力。百老匯的劇場(chǎng)從現(xiàn)在的眼光去看,大多都很陳舊了,但它的舞臺(tái)制作能力并不隨著劇場(chǎng)的老舊而過時(shí)。不用說《歌劇魅影》《芝加哥》這些享譽(yù)世界的大制作了,一些小的制作,都能嫻熟地運(yùn)用舞臺(tái)機(jī)械制造各種舞臺(tái)幻覺即使是如The Wooster Group這樣老牌的“先鋒戲劇”,幾年前創(chuàng)作的《北大西洋》,整個(gè)舞臺(tái)都用鋼板構(gòu)成,而那鋼板在舞臺(tái)上各個(gè)角度都轉(zhuǎn)換自如。
我記得當(dāng)時(shí)就很困惑地問過一位百老匯的舞臺(tái)設(shè)計(jì)師:為什么你們那么愛用鋼鐵作為舞臺(tái)制作的元素?他想了想說,因?yàn)殇撹F比木頭便宜吧!當(dāng)鋼鐵成為舞臺(tái)設(shè)計(jì)的主要元素,舞臺(tái)制作的重要工作,就是要馴服鋼鐵,要讓舞臺(tái)上的鋼鐵,如同軟性材料一樣。我想,這真像是個(gè)絕妙的隱喻:現(xiàn)代舞臺(tái)的工業(yè)化過程,是不是就在這樣馴服鋼鐵的過程中逐漸發(fā)展起來的?
《戰(zhàn)馬》是典型的工業(yè)化
從這個(gè)角度去觀察,《戰(zhàn)馬》是典型的工業(yè)化――也可以說是工業(yè)發(fā)展到很高層次的――戲劇產(chǎn)品。只有工業(yè)發(fā)展到很高層次,它才能夠在工業(yè)的舞臺(tái)上,將手工制作、人工操作的馬的運(yùn)動(dòng),馬的呼吸,馬的故事,嵌入到一個(gè)完整的敘述過程中。
《戰(zhàn)馬》的舞臺(tái)制作高超,并不只體現(xiàn)在舞臺(tái)上如何創(chuàng)造“馬”,而是在整個(gè)舞臺(tái)上,如何才能讓被演員操作的“馬”成為舞臺(tái)的主要表演對(duì)象?如何才能讓這匹有個(gè)性、有生命的馬,在舞臺(tái)上完成一個(gè)總體的敘述?
舞臺(tái)上所有場(chǎng)面的調(diào)控,都是為此服務(wù)的。舉個(gè)最簡單的例子,但凡看過《戰(zhàn)馬》的觀眾,想必都對(duì)《戰(zhàn)馬》的戰(zhàn)爭場(chǎng)面記憶深刻。但仔細(xì)想想,給人印象深刻的、“宏大”的戰(zhàn)爭場(chǎng)面,它運(yùn)用的是什么樣的方法?那幾乎就是在空的舞臺(tái)上,用燈光的閃爍、用幾個(gè)人影的造型,就構(gòu)造了如電影大片一般宏大的戰(zhàn)爭場(chǎng)面。舞臺(tái)上并沒有真的騎兵團(tuán)隊(duì),卻時(shí)時(shí)刻刻有著騎兵團(tuán)隊(duì)的戰(zhàn)馬嘶鳴――人家確實(shí)就只是用簡潔的舞臺(tái)效果營造出龐大的戰(zhàn)爭場(chǎng)面。不錯(cuò),這看上去是導(dǎo)演的構(gòu)思,但如果沒有舞臺(tái)制作的強(qiáng)力配合,這些有可能完成嗎?
從單部作品來說,《戰(zhàn)馬》是一部非常英國的作品。《戰(zhàn)馬》確實(shí)是一個(gè)屬于英國人的故事。在英國人的一戰(zhàn)記憶中,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就是隨著現(xiàn)代戰(zhàn)爭悄然來臨,馬,作為戰(zhàn)爭的重要工具,就從這一時(shí)刻謝幕。一個(gè)新的機(jī)械化的時(shí)代,從此破土而出。它帶來了社會(huì)生產(chǎn)的巨大進(jìn)步,也迅速地讓人脫離與自然萬物的血脈聯(lián)系。《戰(zhàn)馬》是在回應(yīng)這種記憶。而《戰(zhàn)馬》選擇了手工制作的“戰(zhàn)馬”作為舞臺(tái)的主角,我想,也是在潛意識(shí)層面,以后工業(yè)的方式在憑吊前工業(yè)的傷痕吧。對(duì)于我們來說,對(duì)于這一層面《戰(zhàn)馬》的意義,缺少一些潛意識(shí)的共鳴,但這不妨礙《戰(zhàn)馬》仍然是一部感人的作品,更不妨礙《戰(zhàn)馬》對(duì)于我們的重要性。